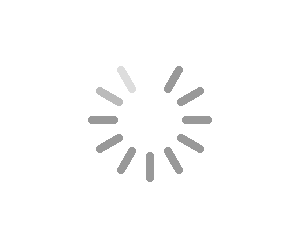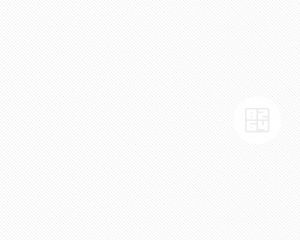来源时间为:2024-01-25
白银往事:“从银河系看过来,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分开”2024-01-2513:38来源: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湃客字号
原创傅淼淼新生活方式研究院
20世纪90年代末,郭龙和张玮玮离开了白银。二人先是去了广东,后又陆续来到北京。在北京,他们加入了野孩子乐队,河酒吧开业后,他们便一直在那里演出和排练。2003年,野孩子乐队解散了。解散之后,他们仍继续做音乐。如今,郭龙和张玮玮都定居在大理。
2012年,郭龙和张玮玮发布专辑《白银饭店》,同名歌曲有一句歌词——“袜子、眼镜、帽子和口罩,四只在白银饭店靠郭龙养活的猫。它们在屋顶,屋顶上很高,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。”
歌词很妙,拉远视角,俯瞰下去,人们确实都如风中的草。在和郭龙聊天的过程中,他向我透露,那四只猫是他住在北京时养的。彼时,他和张玮玮以及舌头乐队的几个人,一起租住在北京霍营的一个小院子里。“在白银那阵儿我天天忙着打架,哪有功夫养猫啊?到了北京之后才开始养,一共养了四只。音乐创作嘛,不可能完全写实,但感觉都是真的。”
白银饭店曾是国营招待所,负责接待从苏联来白银帮忙做基础建设的专家,人们晚上聚在那里吃饭、跳舞,甚至有陪苏联人跳舞的兼职。出生在白银的摄影师李大伟回忆说,他那热爱文艺的父亲,从工厂下班后,会和厂里的工友一起去白银饭店跑场子补贴家用。
郭龙就是在白银饭店接受了早期的音乐启蒙。成年人选择晚上去跳舞,年轻孩子则选择更有性价比的下午场,门票一毛五分钱一张。年轻的小孩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,穿着黄军裤、戴着黄军帽,为了跳舞,甚至不惜逃课。郭龙说:“不同厂子的小孩聚到一块儿,特别容易打架,但也特别容易交到朋友,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听唐朝和黑豹乐队的。”
海明威曾说:“人生最大的遗憾,就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。”郭龙对此心有戚戚。想到曾经一块儿玩的伙伴、曾经暗恋过的女孩,郭龙心里总会漾起一股暖意,但彼时生活在白银,他并没有那么深的感受。“小时候懵懵懂懂,什么都不知道。对白银的很多感受,都是在离开白银后产生的,等长大了、离开了,再回过头看,才慢慢理出思绪,那时候可真美好。”
如今,郭龙和一群玩音乐的老朋友生活在大理,偶尔才回一趟白银。“印象中很漫长的一段路,现在走几步路就到了,街道也变了样,甚至跟记忆中的方位都产生了偏差。”走在故乡的路上,他竟然生出了异域感,就连和曾经最熟悉的小伙伴,也只剩下客气的寒暄。
某个时刻,故乡似乎成了陌生之地,有新的故事和新的生活,很难再参与进去。但深入肌理的联结并没有那么容易斩断,郭龙说:“我的青春,我的世界观、价值观,全都是在那里发生和建立起来的,这些东西塑造了我,且永远都不会变。”
20世纪80年代的白银,不同的厂矿间形成不同的生态,有不同“派别”的“厂矿子弟”。出门在外,人们都是论厂分人,年轻人拉帮结伙,没有什么娱乐,最爱的就是打架。其实大家没什么利益冲突和经济瓜葛,驱使人们发起争端的,更多的是荷尔蒙冲动。彼时最流行互相抢黄军帽,郭龙说,要是戴一顶新的黄军帽去学校,却没什么实力加持,那么不用想,不超过六小时,黄军帽肯定会被抢走。
郭龙30多岁时,还经常做噩梦,梦里他一个人走路去上学,突然围过来好几个人要打他。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被欺负的,有时想在兜里装几毛钱,他都得想方设法塞进鞋垫里,而一旦鞋垫里的钱都被翻出来,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教训。
“十五六岁上学的时候,大家的心思早不在学习上了,书包里可能不装书,但一定会放一把刺刀。没办法,大环境就是那样的,你不反抗,就只得挨打。每天走在路上都有人会抢你,一到放学,校门口总有几帮人堵在那里找茬。这几乎已经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了,以至于我成年之后,还经常做噩梦,梦到这些画面。”
那个年代似乎都是这样,就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演的那样,孩子们每天打来打去的。即便挨了欺负,他们也不好意思告诉家长。在郭龙眼里,挨欺负了找家长,是一件非常没出息的事情,关键是告诉家长也没用,家长总不能不上班去跟小流氓交涉,所以他小时候唯一羡慕的事情就是有哥哥。但他没有,他只有姐姐,还要保护她们。挨了几次欺负之后,郭龙决定奋起反抗,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掏走一分钱。之后,他在一次“战役”中一战成名,自此,没人敢再欺负他。
郭龙比张玮玮大一届,甚至一度欺负过张玮玮。聊起这段,郭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“我那时候在我们那片儿已经挺有名了,我其实没怎么欺负他,无非是让他见面时给我带根烟,他就从他爸那里偷一根,给我带过来。后来有天,我去他家里,发现他家居然有台钢琴,他坐下来,给我弹了一首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,当时我站在旁边,整个人几乎都要疯了。我心想,这也太美好了。那天之后,我跟身边所有兄弟说,以后谁也不允许欺负玮玮。”
郭龙(右)和张玮玮(左)在江边。(图/安娜)
二人共同打架的往事,早已被讲了太多遍。他们一起打过很多架,这不仅令他们“声名远扬”,更增进了彼此的信任,友谊越发坚固。但这个故事里一直有一个被忽视的细节,那就是两个正值青春的男孩,表面上喜欢打架斗狠、义气兄弟之类非常江湖的东西,但骨子里都在偷偷喜欢文艺。
“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,我们会聊音乐和小说,聊他最近学会了哪些钢琴曲、我看了哪些书。但其他兄弟在的时候,我们从来不聊这些,别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,我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。我喜欢看科幻小说,小学时就把凡尔纳的‘科幻三部曲’看完了,后来又开始看金庸。我跟玮玮一起看《笑傲江湖》,我们都特别喜欢令狐冲,觉得他特别潇洒,十几岁的时候总梦想能成为他。遇到做选择的时候,我会想:如果是令狐冲的话,他会怎么选?后来,我们又一块儿喜欢王小波,做选择时就会想:如果是王小波的话,他会怎么选?再后来,我们又一块儿看了很多王朔的作品。”
郭龙喜欢从星座的角度解读二人性格上的契合,诸如:张玮玮是摩羯座,非常理性,自己是巨蟹座,非常感性;张玮玮非常自律,做事很有计划性,而自己则非常随性,一切顺其自然。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欠缺的东西,性格十分互补。
或许,这些不过是老友间的笑谈,进一步作为二人兴趣相投的佐证。实际上,两个人能一直是好朋友,总会有更深层次的理由,那就是“我们两个人打从心底希望对方好,即便在我都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,他也永远不会放弃我,反之亦然”。
2023年,杭州草莓音乐节上,郭龙看到大运河杭钢公园里钢厂的大烟囱,附近厂房的墙上还留着标语,突然心生唏嘘,感觉有些失落。他一个人在附近转悠了半天,想起白银的生活,想起空气中弥漫的机油味道。
郭龙时常会想起一个故事——森林里,有只兔子一直在跑,撞到了一棵树上,树上掉下来两只狗,之后,两只狗也开始跑,它们去追一只熊……人们听到这个故事,思路总会跟着走:树上怎么会掉下来两只狗?为什么又开始追熊了?熊从哪里来的?最后追到了吗?但故事讲到最后,问题是:兔子去哪儿了?
郭龙总会问自己,也问张玮玮:兔子去哪儿了?在白银,他们是偷偷喜欢文艺、喜欢打架的懵懂少年,后来,他们离开了那里。如今,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?二人还行进在同样的道路上吗?郭龙感慨:“永远不要忘了最初的那只兔子。”
网易云《白银饭店》下面有一条高赞评论:“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会聚在这个黄土高原戈壁滩,操着全国各地的方言,用堪比原子弹的大爆炸,炸出了一个叫作白银的城市。曾经共和国铜冶炼的翘楚,白银,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。”
郭龙回忆说,他小时候的同学们,什么口音都有,讲得最多的是上海话,因此,他从小就能听懂上海话,如今听起来,也毫不费力。他听同学讲述父辈的故事——年轻人某天突然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名字,要去支援大西北。很多人都以为只去三四年,但火车停靠兰州站之后,车站门口停着很多军用大卡车,年轻人坐在卡车后斗里,被拉到四面八方,卡车停在哪里,他们就建设哪里,孩子也生在那里。一眨眼,一辈子就过去了。
郭龙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,他的父母都是学工科的。郭龙的父亲不爱说话,但性格十分开朗且包容,他喜欢钻研各种好玩的东西,带着郭龙做风筝、滚铁环、玩火柴枪,还用车间里废弃的材料给郭龙做了一辆小钢车。游戏机刚风靡时,父亲也会带郭龙玩,他甚至用私房钱给儿子买了一台游戏机。科幻小说也是父亲推荐给郭龙的,父亲有很多书,他可以随便看。郭龙的妈妈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,所有的朋友来他家里玩,都能得到盛情款待,孩子们早上一睁眼,一碗荷包蛋面条就端到嘴边了。
彼时,白银的工资是全甘肃省最高的,孩子们穿着也很时髦,很多东西刚一流行,白银的小朋友就能吃上、用上,有时甚至比兰州还要早。各大工厂的福利也都特别好,一到节假日就发米面油,秋冬时节还会发秋裤。有的工厂会办小学,在里面上学的“厂矿子弟”,只需要交金额很小的书本费。夏天厂里发西瓜,一次性发几十个,能把床底下塞得满满当当。夏天厂里还会发酸梅汤,工人们提着水壶去打,想打多少都可以。郭龙感慨:“我再没喝过那么好喝的酸梅汤。”
郭龙记忆里的爸爸妈妈,也都很年轻,每天高高兴兴。郭龙家里买了全厂第一台电视机,当时几乎半个厂的人,都挤到他们家来看那台16寸的黑白电视。到现在,他还记得那台电视的壳子的颜色,橘黄色的,就像他回忆起白银时,脑海中会自动加上一层暖黄色滤镜。
时间的指针拨至20世纪90年代,工厂响应国家号召,开始寻求转型,曾经日夜轰鸣的机器突然停止了运转。李大伟感慨:“白银的经历,跟所有面临转型的工业城市一样,这些故事已经被讲过太多遍了,似乎生活在工业城市的年轻人,生命经验都能感受到某种相似性,父辈都曾经历过困顿和迷茫。有人抓紧机会往外跑,逃离眼下的困境;有人扛住压力,努力地过活,坚守在此处。”
震惊全国的“白银杀人案”,就发生在那个时段,这给白银人本就艰难的生活,罩上一层巨大的阴影。白银警方几乎对白银全部成年男人做过指纹采集,郭龙也在其中。这一切,正如张玮玮《关于白银》文章里所写:“在凌乱中挣扎的每个白银男人,都曾替高承勇背负着‘变态’的猥琐嫌疑。”
当地人聊起这个案子,总是难掩愤怒,摄影师李大伟说:“这么说吧,白银是一个有着固定游戏规则的地方,那就是‘三点一线’做工人,他们大都老实本分,是流水线上高度工业化的一分子。”
说罢,李大伟咬着后槽牙骂道:“好恨!”
郭龙有两个姐姐,每当姐姐上夜班,郭龙就和爸爸一起护送。护送完姐姐,郭龙会叫上七八个男孩,四处巡逻。
“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晚上都会去汽车站、火车站、铁道边,还有公园的黑暗角落转悠。那时候我们正值青春期,身上有一股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,心想,要是能亲手抓住凶手该多棒啊。”
几十年后,“白银杀人案”的凶手终于被抓。看完新闻,郭龙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凶手打过太多次照面,他经常在凶手经营的小卖店买东西,甚至跟他赊过烟,“顶着一张扎在人堆里就完全认不出的脸,想想真是魔幻”。
我是在2023年7月底的一天出发去白银的,从兰州汽车东站售票窗口买票,25块钱一张。买完票进站上车,不到5分钟,客车就发动了。
车里正在放抖音上流行的《狂浪》:“狂浪是一种态度,狂浪是不被约束,狂浪,狂浪……”我放好行李,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隔壁座的小朋友正在兴高采烈地跟唱“恐龙扛狼恐龙扛”,我想告诉小朋友,这跟车里放的其实是两首歌,但最后只冲他笑了笑。
汽车行进了大概20分钟,窗外开始飞速掠过连绵起伏的群山,司机师傅关掉了音乐,车内突然变得格外安静。小朋友伏在妈妈身上睡着了,没多久,后座也传来呼噜声。我戴上耳机,随机播放